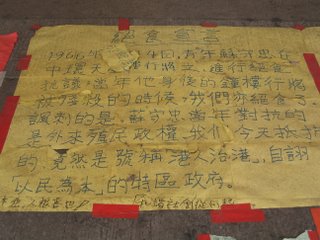中國人是個逃難的民族,幾千年來的傳統,造就了這個移民社會。戰後嬰兒潮的一代,不少父母避秦南來,在這塊殖民地尋找到一個安樂窩,踏實在這裏建立事業,組織家庭。
南來的一代,雖然逐漸在香港安頓,但心卻繫着北方的家國,鄉土情愛國心,內地接連的政治動盪,椎心泣血但無能為力。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,糧油藥品,衣物匯款,不絕的接濟內地至親,以解燃眉之困。人在香港,心仍眷戀着他們的故鄉。
戰後的一代,幸運地搭乘經濟起飛的順風車,事業經濟剛有所成,適值香港前途不明,再加上八九屠城震撼,逃難的DNA 又一次發作,數以十萬相計移民,入籍美加紐澳買個政治保險。雖然回歸後,不少人又再連根拔起回流香港,當中不少只為搵食需要而回來。事實證明,南來避秦的上一代和戰後成長的這一代,都沒有視香港為他們真正的家,沒有穩固地紮根香港,從沒有為香港打拼的想法,有任何損害自身利益的風吹草動,唯一的選擇,千方百計,溜之大吉。
到了朱凱迪、陳景輝這批三十歲不到的一代,香港前途問題出現時,他們還未出生,或許只有幾歲,姑且稱他們「香港前途的一代」。他們沒有南來一代的歷史包袱,也沒有嬰兒潮一代的經濟條件。比起上兩代人,年輕人對香港有更深厚的感情,有更真誠的歸屬,有更熱情的投入。過了半個世紀,這一代香港人不想再四處漂泊,要真正紮根香港, 「香港是我家」不再是虛偽的口號包裝,而是行動實踐。
他們認真地研讀這片土地的過去,發現當權者的論述與真實有很大出入。殖民者和特區政府的管治模式和理念,根本沒有絲毫的變化,都是摧毁過去來創造地產商口袋裏的財富,都是以鏟除歷史來模糊人民的記憶,都是以諸多荒謬的理由來阻礙民主的進程。面對不義和不公,年輕人不再只是把臉別開或逃離現場,真正的本土運動,由這一代開始。
明報 2007-08-12